
楼兰出土西晋十六国简纸书迹研究

残纸与孔侍中帖比较▲
楼兰出土西晋十六国简纸书迹研究
一、曹魏末期至西晋前期木简书迹
楼兰遗书含纪年的简纸有魏“景元、咸熙”、西晋“泰始”等年号。晋武帝司马炎265年末废魏改晋,年号“泰始”,边远的西北地区信息不畅,仍沿用曹魏“咸熙”年号,楼兰简纪“咸熙二年、三年”者,即西晋“泰始元年、二年”(265、266年);写有晋武帝年号的从“泰始二年”一直到“泰始六年”,另有少量西晋“永嘉”(307—313年)纪年残纸。
楼兰简纸文书里时代最早的木简之一——魏景元四年简(沙木738,263年)属较成型的行书字迹,其笔画较多规律性的行书化钩连,末笔具下引、牵发之姿,比如“景、索”下的“小”、“兼”下的“灬”连成“一”。其成熟的字形笔画等比稍晚几年的泰始年间简书并不逊色。

有“泰始”纪年的几件木简中,有些或出于一人手笔,如沙木725、728、729、735、736,孔木50、65等;纪年为“咸熙三年”的孔木51、64亦为同一人所书。这几件简书代表当时较典型的西北民间墨迹形态,它们走出早期楷、行书“多体混杂”的时代,其今楷、行书体态大致定型了,一望而知是行、楷书,而非东汉末那种既楷且隶的不成熟状态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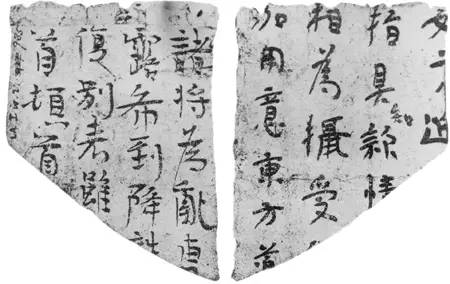
二、西晋后期残纸墨迹
自西晋初木简到西晋末残纸,仅越过40多年,但新体成熟脚步颇快,楷、行书构形的集体性转变大体完成。新体另一明显标志是字态一律左倾(单字左低右高)。西晋间另一个重要变化是书写材质变化:简牍日渐退出,纸质渐成主角,楼兰遗书中,木简大多属曹魏及西晋前期之物。
三、楼兰西晋简纸与郴州西晋简牍比较
湖南郴州出土的西晋简牍时间为西晋惠帝(290—307在位)时期,与西北楼兰西晋简纸处于同期。
郴州西晋简以楷书为主,楼兰西晋简纸以楷、行为主。拿郴州西晋简与楼兰木简比较,它们楷化进程大体相当,笔触上,西部书迹显得厚重,秃钝型笔画较多,郴州简则秀逸端庄;结字上西部墨字各式各样、良莠不齐,郴州晋简则工整规范、今楷技巧似更熟练——这并非地区性演进的差异,而应归于书写技术上。两种墨迹一处西北,一处南方僻蛮之地,相距不啻万里,然而两者对新体楷、行的表现可谓殊“法”同归,在楷、行技术表现上大体一致。西晋间中原士人尚未大举南迁,各地新体的普及,一方面来自三世纪前叶中原士人新写法(如锺繇等)的辐射影响,另一方面归于社会实用书写对新体的自觉推进、发展。西晋时期,大江南北新体的进展程度大体相当,至少在永嘉之乱前如此。

五、西部残纸中的十六国前期墨迹研究
北方的十六国与江南的东晋处同一时空,东晋士人书法家的作品为后人津津乐道,庾、王、郗、谢氏等代表的晋人书法被后世追崇效仿,亦为帖学渊薮。同时代的北方书写是什么样子?五胡乱华,战事频仍,国号变幻,十六国时期存留系统的、大宗的书迹较少,西北纸简书迹为我们提供了窥探北方书写的材料。

总起来看,楼兰纸文书展示的十六国前期墨迹,既有含有古意的写法,也有非常成熟的新体楷、行、草。将这些西北书迹和江南书法略加勘比后,我们可以做出以下思考:
一是,南、北新体发展进程的一致性。此时期南北大分裂、大动荡,而字体演进仍然继续,南北各地文化乃至书写的流布互通并未真正中断。从东晋诸种墓志、二爨与北方碑铭的共通性,到敦煌遗书中数件王羲之《十七帖》临本(虽然时间较晚些),等等,表明南北书法的持续交融。一般认为江左书体演进与书法行为依循常态、更代表主流和先进性,其实北中国未见得落后多少。北方政权迭替频繁,似乎文事荒芜,但西北纸书墨迹告诉我们,这里书法发展同样持续不断,西北残纸与江左名家的诸多相似处足以证之,若得见十六国前期北方名家崔悦、卢谌(均活动于三世纪末到四世纪前叶)等,想必也是江北领新体风骚之属。如上所述,郴州、楼兰的西晋墨书何其相似,其楷、行的成熟度几近一致。新体的主导与古法的遗存,于南北各地都同样存在着,新体普及是大势。而铭石书系统属另一种情形,南、北方的铭刻完全承汉魏旧法,与手写体不能同日而语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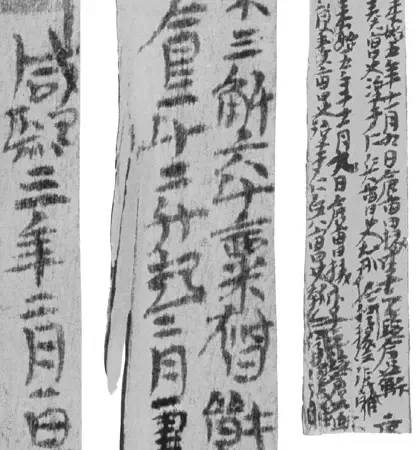
二是,时代风气大体一致,表现在构字、用笔、气息诸方面的一致性,这是书体演进历史与书写环境决定的,亦即说,在那个时代,不管是名门士人还是基层胥吏、平头百姓,他们笔下总含有近似的格调、情趣,包括笔墨技巧与作品气息。陆机《平复帖》在楼兰纸书中能找到不少类似的笔触表现(如孔纸19.6、孔纸26.1等);《九月十一日纸》(孔纸24.2正)与王右军手札何等相似;王右军《十七帖》,于沙纸929、孔纸31.8及一些习字纸中可找到近似草法;王珣《伯远帖》可以在《李柏文书》(橘纸538a)、《济逞白报》(孔纸7正)等作品中发现相似技法;启功先生说:“至草书之奇者,如楼兰出土之《五月二日济白》一纸,与阁帖中刻索靖帖毫无二致,‘无缘展怀’一纸则绝似馆本十七帖。其余小纸,有绝似锺繇贺捷表者。”……后人所谓的“魏晋风度”,在魏晋南朝名家身上得以系统性体现,其实这种“风度”在西北残纸上亦能觅得,乃时代风气使然,与其说这是东晋名家书写艺术与精神品性的追求,不如说是文字书写特殊阶段历史规定性所决定的,换言之,汉末魏晋字体演进的特殊情形,使新体逐步成熟,同时古体(篆隶等)并未彻底褪尽,新、旧元素并存于当时社会书写中,其特征反映在笔画和组构间,令字迹呈现着独特的气息。所以晋书“潇洒”韵致不止于士人名家,而具有时代性、普遍性,这在西北残纸中也嗅得出。
三是,名家的个性风格离不开社会基础。西北残纸显示了书写面貌的丰富多样性,其中不乏与东晋名家作品相近的样式——有的还早于江左名家时代。名家技法与风格不是孤立突出的,他们一方面有其传承谱系,如锺、卫、王、羊等,另一方面不得忽略社会性书写的基础作用,如东汉末新体发展与同期刘德升、锺繇之间关系那样,个人与社会、名家与基层书写间相互影响、互为作用。西晋至东晋,从卫瓘、张华、陆机到庾亮、王导、郗愔、王羲之、王献之、谢安……新体愈来愈成型并臻于艺术高峰的脚步清晰可见,然而王右军们不是孤立的、高高在上的,其实当时整个社会都在写类似王导、王右军们的书体,只不过王右军们拥有更高超的技术、更广博的素养并多有创造,从而成为时代的代表。总之东晋名家无法脱离时代总体风格特征。

四是,社会书写间的差别,体现在用笔风格上(如粗厚笔触型,出锋显芒型,古朴型与雅逸型)、新旧体含量上、技术(高低)层面上等等。字体演进尚未彻底完成的历史阶段,不同书写群、不同写手笔下的墨书各不相同,因此也形成此期墨迹风格丰富多彩的局面。
七、楼兰残纸中的练字纸
楼兰文书中的练字残纸不少,绝大多数为纸质,时间大多为十六国时期,我们将这些练字纸做简要书体统计,统计显示其书体集中于今草、行、楷,隶书、章草极少,草、行、楷三体比例大体持平。练字纸说明当时人们练书习字之风非常盛行,而且大家主要在苦练新体楷、行、今草,亦可佐证新体流行程度。
孔纸31.2正背均为习书字迹,至少出于两人手笔。该纸背面以楷、行书为主,另有几个草字。其楷字属今楷法,行笔坚定粗犷,几个“顿”的“页”之横折部颇另类,像“丁”形,似两笔写成,而非规范的折部写法;点线没有过多藏、调锋类动作,显得直截了当。该残纸正面则出于另一位书者,“首、白、汹、无、十”等楷字顿挫分明,点画起止颇显规矩,很有锺繇、二王楷书的技巧与风致;纸右中部的“十月九日白”等大字笔画粗重,竖笔折逆锋起笔,讫笔回隐锋,行锋有迹而毫芒不显,横画起止无痕,润泽含蓄,可谓典型完美的横、竖笔;这几个大字看上去和左部的“首、白、汹”等字虽不相似,其实应是一人书写,这从“白”字写法可以看得出,特别是“白”首画“丿”的写法——同一书者训练一种书体(如楷书),且同样工谨书写,也会有不同面貌。古人操毛笔书写,日夜为之,一生为之,甚至“忘其疲劳,夕惕不息”,他们笔下的墨迹世界远比我们以为的要丰富,一个民间普通书手或基层胥吏,能够写出不同风格的书迹,这很自然。这种情况既给今人探究古代墨迹以丰富的实物资料,也因其书迹复杂性常令人困惑,今天的研究者须以多样性的、流变的、发展的、辩证的观念看待字体尚处于变动期的古人书迹,像孔纸31.2这样,背面朴拙的字迹和正面新妍的笔法并不代表它们有时间先后之别(它们基本是同时期字迹),该纸正面妍俏、粗厚两组楷字其实出于同一人之手。

同近期字体“新旧”间的差异也在习字纸上反映出来,这些纸书大多为十六国前期之物,时间间隔并不大,这种“新旧”之别实属个人书写技巧与习惯上的。孔纸33.2背面中下部的大字,粗长捺笔如扫帚般不成型,竖笔一拓直下含隶意,“及”的“丿”头尖尾粗——书写水平低劣、旧有写法的惯性影响、新体技术的不成熟不到位等,造成这种情况。
从当时识字习书的重要范本《急就篇》的练习残纸,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新、旧体仍存在不同的认知和接受程度。楼兰《急就篇》残纸由马纸171、172、173等残片组成,正背面皆为《急就篇》起首部分。正面似为范本模样,用了两种字体:先是四行含隶意的楷书,再用章草重写之,似乎在以正、草两体做示范。背面为习书者笔迹,基本依正面楷字模样照写,写得朴拙稚气,且字体较大。《急就篇》作为汉代传续而来的字书,其古体(隶、章草)特色一直比较浓郁,即便到了新体流行的魏晋时期,人们习写《急就篇》时仍以隶意为之。楼兰《急就篇》残纸正背两面的正体字,是以时书(今楷)抄写本应是隶书体的内容,或是对隶体母本的楷书化理解、发挥,于是才有了这种兼楷兼隶的字迹。该残纸正面草字为含波磔的较规范的章草,应是基本依照旧母本(有可能出自汉末或更早)之法所书,或表明魏晋时代古体草书在人们心中仍占相当分量。
关于习字所依据的新体范本,有研究者认为必是由内地传入西北边垂的[26]。我们认为,习书范本应是多种多样的,来源也是多渠道,包括内地传入和当地楷模。其主要的背景是,新体楷、行、今草的发展成熟,自中原至边远地带,汉末三国西晋间,大体依同步进变态势;同时期同地域内,有着新、旧写法的差异,这在海内各地都存在着;诚然,比较而言,中原地区的新体发展应有一定的引领作用;从书写主体看,士人名家的楷范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。河西地区东汉即是书法、特别是草书发达地区,之后,早期楷、行、今草在这一地区的发展也不会落后于其他地区,例如,“兰州伏龙坪东汉纸书”(早期楷书),其新体含量不亚于同近期的东牌楼简牍。在书家之名人效应尚未步入热潮期的西晋以前,中原书家的影响虽然存在,但不是唯一的示范标杆。所以西北地区人们学书取法,既有内地楷模(名家书迹以及官府公文、书信等),也应有当地的书写楷则。
免责声明:如有关于作品内容、版权或其它问题请于作品发布后的30日内与我们联系。
